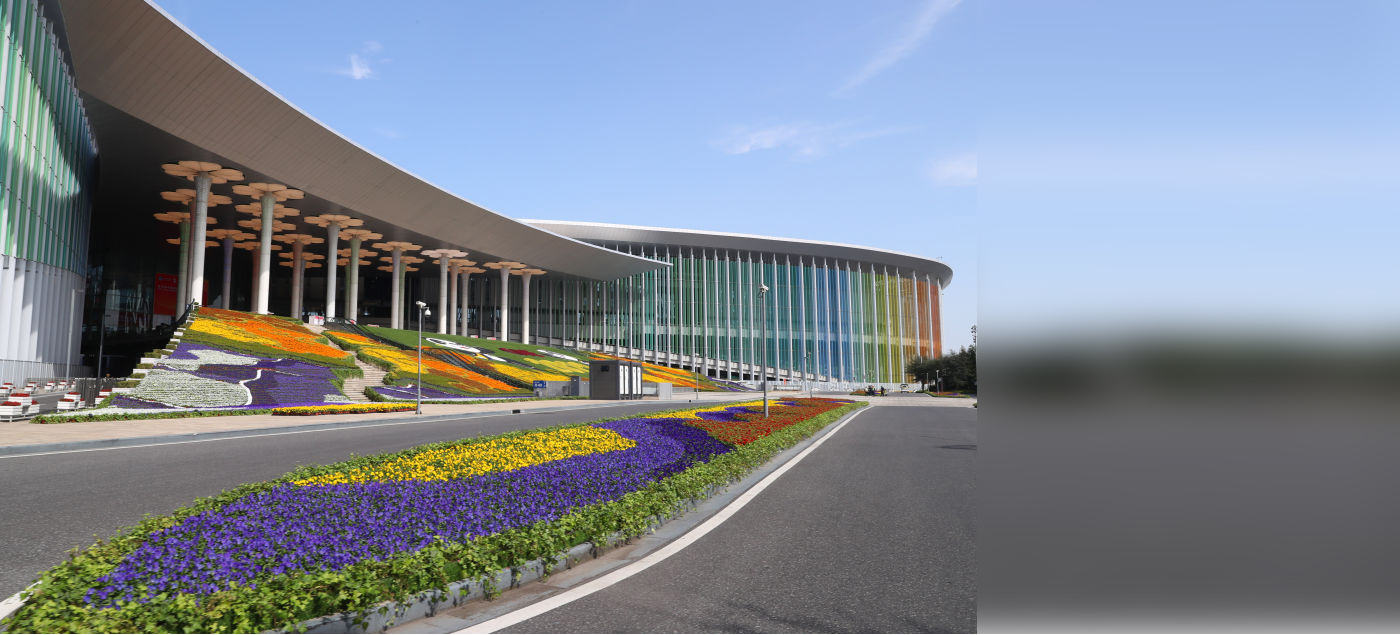只是喜欢 | 报纸往事
1990年的暑假,我经常一个人背着相机,在南太行的深山里转悠。
顺着山坡下到谷底,再爬上另一个山坡;沿着小溪钻进深山,看到巨大的瀑布;坐在悬崖边上扔下去一个易拉罐,又看着那个空罐子被山谷里的风卷着送回手边……

▲威廉·莱布尔:《乡村政治家》,1877年,德国温特图尔美术馆
那年我上初一,喜欢呼朋唤友,也喜欢独来独往。
我背着一台120的海鸥,拍过挑着山楂汽水上山的农夫,柿子树下眺望远方的少女,围坐在银杏树下烤火的僧人,草丛中一只东张西望的松鼠。
山谷里有一座废弃的水坝,水坝下面躺着一块有凹槽的巨石,凹槽里有清水,像一个浴缸。
我躺在里面,看着四周连绵的群山和上方无尽的苍穹,仿佛世界只剩下我。

▲保罗·塞尚:《读报纸的父亲像》,1866年
当你长时间地看着天空的时候,慢慢会发现天空并不只是蓝色,云朵也并不只是白色。
那里面会有一点紫色,一点绯红,一点亮黄,一点青绿,缤纷斑斓。
不知什么时候,一只色彩奇异的小毛毛虫顺着石头爬到眼前。
我刚一触碰,手指就刺痛不已,红肿起来。
方知自然界里每一个存活下来的生命,都绝非等闲之辈。
好吧,领教了,胶卷也用完了,太阳也下山了,收工回家。

▲陈洪绶:《校书图》,明
那时候,出门时兜里装着足够的胶卷是多么巨大的满足啊!
回到家天已黄昏,把窗帘拉得严严实实,用一块红布把手电筒包住,我的小房间就成了简易的暗室。

▲夏加尔:《斯摩棱斯克日报》,1914年
冲洗胶卷是个技术活。
要把胶卷一圈一圈缠在卷轴上,每一圈之间要有间隔,一旦粘连就报废了。
然后装入不锈钢的密封罐子,倒入药水,缓缓转动。
洗好的胶卷夹在院子里的铁丝上,一条条在微风中晾干。
洗照片的设备很简单:一个自制的曝光箱,百货大楼买的药水和相纸,最豪华的是一台舅舅送我的放大机。
120的底片不需要放大机,直接和裁好的相纸叠在一起曝光,然后把相纸放在显影液里,用竹夹夹着轻轻晃动,看着图像一点一点浮现出来,再放到定影液里稳定。
刚洗出来的照片湿漉漉的,软绵绵的,需要贴在玻璃上晒干。
如果有烘干机就方便许多,不仅可以快速烘干,还可以使照片更有光泽。
最后一步就是裁剪了。把照片四边修剪整齐,也可以剪出小波浪的水纹,还可以在底部留一些空间写字。

▲雷诺阿:《读报的克劳德莫奈》,1872年
那一年夏天,我冲洗了数不清的照片。
我选了其中一些,在A3纸上完成了暑假作业——一份手抄报。
那是一张真正的全部工序都由我手工完成的报纸啊。
我用水彩笔勾勒了大标题《我们是跨世纪的一代》,并把树下女孩的照片裁剪后作为配图。
这张小报开学后被贴在展板上,放在教学楼前最显眼的位置,整整一周。

▲杨子华:《北齐校书图》局部,南北朝,波士顿美术馆
那时候,我没有想到,21世纪拍照如此简单,分别不再伤感。
那时候,我没有想到,21世纪比想象丰富,也比想象单调。
那时候,我没有想到,所有人,还是所有人,谁也不会改变。
那时候,我还不懂得珍惜,没有想到21世纪的我,是如此怀念那台再也找不回来的海鸥相机,和我的第一张手工小报。
#作此文想到了这些画
或者是看了这些画作了此文:
胡安·格里斯:《水果碟子、书籍和报纸》,1916年,私人收藏
保罗·塞尚:《读报纸的父亲像》,1866年
威廉·莱布尔:《乡村政治家》,1877年,德国温特图尔美术馆
威廉·莱布尔:《读报的人》,1891年,弗柯望博物馆
雷诺阿:《读报的克劳德莫奈》,1872年
夏加尔:《斯摩棱斯克日报》,1914年
夏加尔:《报贩》,1914年
杨子华:《北齐校书图》,南北朝,波士顿美术馆
陈洪绶:《校书图》,明
王齐翰:《勘书图》,五代十国,南京大学
王蒙:《琴书自娱图》,元,台北故宫博物院
黄筌:《勘书图轴》,五代十国,台北故宫博物院
佚名:《勘书图》,南宋,台北故宫博物院
佚名:《十八学士图之书》,明,台北故宫博物院
黄慎:《牛角挂书图》,清,弗利尔美术馆
拉图尔:《木匠圣约瑟》,1632年,巴黎卢浮宫
#可能比较搭的音乐
莫扎特:《费加罗的婚礼》(当微风轻轻拂过)
小约翰·施特劳斯:《维也纳森林的故事圆舞曲》
普契尼:《今夜星光灿烂》,《托斯卡》第三幕,咏叹调
张新彬
迅即行动抓落实——郑东新区龙湖办事处筑牢项目工地疫情防控安全屏障
上街区这所学校学生劳动技能拉满:醋焖肉、挖红薯,动手能力提升全面成长
习近平向国际竹藤组织成立二十五周年志庆暨第二届世界竹藤大会致贺信
《中国网信》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指引推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纪实》





 联系记者
联系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