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一辆单车,大姑送的,剑鱼牌——天蓝色的神气小车。
那是小学四年级,有了单车助力,我们的周末就像插上了翅膀。
我们在夏天的河堤上比赛,骑的最快的傻大个儿一头扎进沟里;
我们沿着河堤骑很远很远,发现一大片西瓜地,驻扎在河边的汽车连,空地上还有一架直升机;
我们骑到中同街,用粮票换币打捉虫敢死队和一九四三。
大头在操场上表演大撒把,结果摔了个嘴啃泥,牙呲在水泥地上磨掉半个,天天咬着牙往外呲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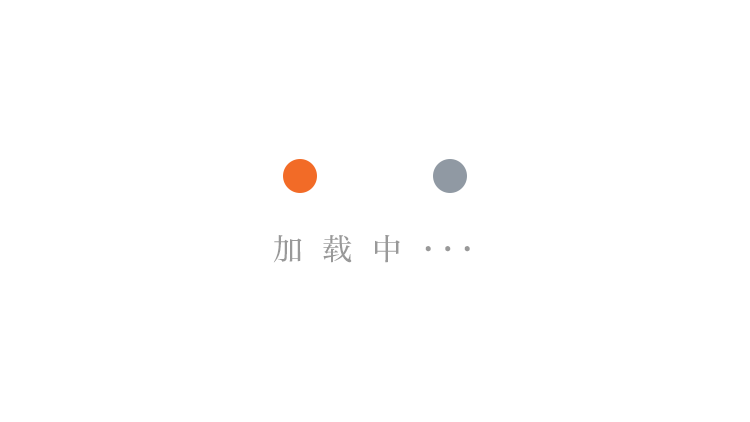
▲罗伯特·梅德利(Robert Medley):《周末的自行车聚会》
到了中学,同桌是个高挑开朗的女生。我们都读汪国真,放学经常成群结队的骑车去文化宫吃雪花酪。
但有一阵那个女孩突然莫名其妙的生气,费尽周章才搞明白:人家骑车带女朋友都是坐横梁上。
这样啊,天呐,我们这是在谈恋爱吗?
那就坐横梁吧。
只是她的个子有点高,还总是昂着头挡住我的视线,左顾右盼全然不顾危险,这让我大为气恼。
不过很快她就转学了,我们大部分时间只能互相写信,把收信人和寄信人地址反过来写,这样就可以不贴邮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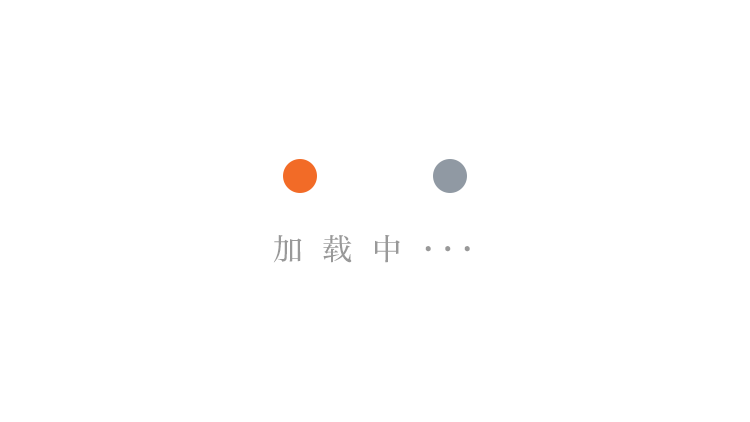
▲费宁格:《自行车赛》,二十世纪初,德裔美国画家
高考前我们约好在牧野公园见面。
她穿着一件黄色的连衣裙,骑了一辆雅白色的单车。
停车时那辆单车翻倒了,她看都没看,就在明媚的阳光里笑盈盈的向我跑来。
那一年我们十七岁。
那时没有网络,没有手机,我们仅凭书信,去赴每一次约。
我们骑着单车穿过树林、穿过阳光、穿过风、穿过雨,我们可以一直骑到三十公里外的苏门山下。
谁在乎呢?要到二十年后,才会在一些夜晚被曾经的纯真侵袭,一点点扎心的疼痛。
那样简单的世界,竟然再也没有回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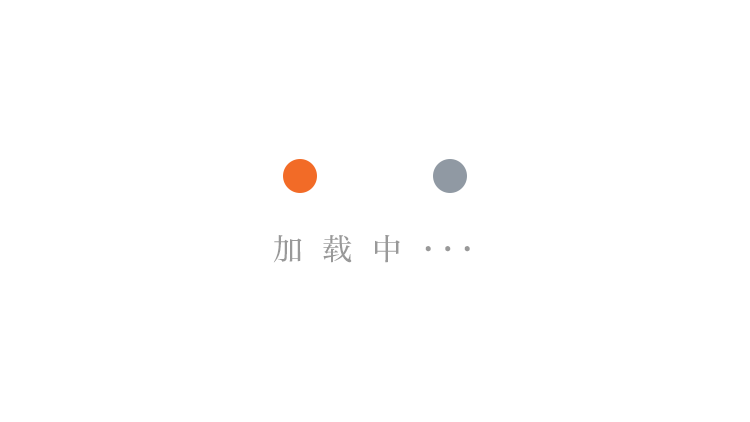
▲娜塔莉亚·冈察洛娃(Natalia Goncharova):《骑自行车的人》,1913年,俄罗斯
在大学里,有一次课后发现车没了。过了几天,看到一辆车没有锁,就骑走了。
我从来没有锁过那辆墨绿色的单车,停在教学楼边、食堂门前、宿舍楼下,然而它的主人却消失了,再也没有出现。
那时我就想,校园里所有的单车都不要锁,谁需要就骑,骑完就放在原地。
多么伟大的创意啊!可惜那时的网络,还处在拨号上网的阶段。可惜我,从来都不是一个创业者。
想象中的我,要比现实中的我完美太多。要等到在社会中被重捶过,才明白行动胜过千言万语。
那已经是很久以后了,好在人生何时上路都不为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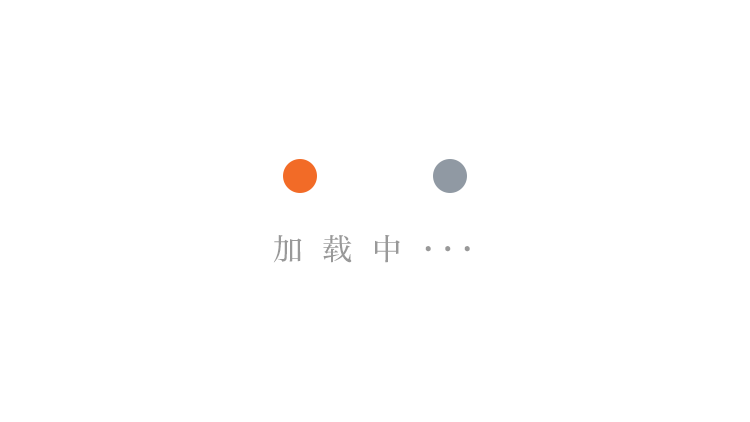
▲杜尚:《自行车轮》,1913年,纽约现代美术馆
在那之前,我骑着单车跑遍了新乡,跑遍了郑州,跑遍了上海。
在火车站碰到一辆出租车,被那个胳膊上纹着青龙的大汉讹走五十块钱;
在烈日下骑的汗流浃背,坐在桥头一个小摊前要了一碗凉粉,不知为何摊主阿姨坚决不收我的钱;
在傍晚的苏州河边,坐在单车上看斜阳晚照,不知去留,进退两难。
在那之后,日子密的像雨、快的像风,单车已经从生活中消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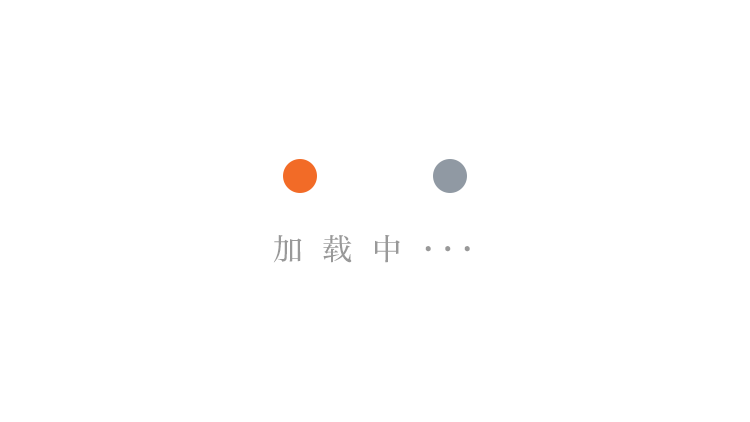
▲唐寅:《红叶题诗仕女图》,明,私人收藏
直到有一天,在郊外偶然看到堆积如山的共享单车,想起我那曾经每天反复擦拭、给链条上油、调节闸线、扛着上楼、因车铃被偷和看车人大吵一架的单车——
如今像垃圾一样密密麻麻的堆在荒郊野外,才猛然意识到这些年我们经历了多么巨大的变化!
珍贵、低廉,巨大、渺小,错对、是非,不经意间已完全转变,如此魔幻。
但我并不想回到过去,虽然十七岁的单车还会在梦中响起清脆的铃声,但我已没有力气、没有勇气,再来一次。
作此文想到了这些画
或者是看了这些画作了此文:
周文矩:《观舞仕女图》,五代十国,弗利尔美术馆
杜尚:《自行车轮》,1913年,纽约现代美术馆
翁贝托·波乔尼:《骑自行车者的活力》,1913年,意大利
让·梅辛格:《自行车上》,1912年,法国
费宁格:《自行车赛》,二十世纪初,德裔美国画家
娜塔莉亚·冈察洛娃(Natalia Goncharova):《骑自行车的人》,1913年,俄罗斯
罗伯特·梅德利(Robert Medley):《周末的自行车聚会》
威廉·德·库宁:《女人与自行车》,1952年,纽约惠特尼美国艺术博物馆
波斯画师:《尼诺·厄里斯塔维肖像》,1829年,格鲁吉亚第比利斯国家美术馆
埃德蒙·布莱尔·莱顿:《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维多利亚时期,英国
夏加尔:《歌剧院》《蓝马》,1954年
唐寅:《红叶题诗仕女图》,明,私人收藏
狩野长信:《花下游乐图屏风》,东京国立博物馆
费丹旭:《探梅仕女图》,清,旅顺博物馆
佚名:《执瓶仕女图》,清
吴湘:《树下停阮图》,明,旅顺博物馆
詹姆斯·格恩:《穿着黄色连衣裙的波琳》,1944年,哈里斯美术馆
雷诺阿:《女人半身像》,1883年
查尔斯·爱德华·佩鲁吉尼:《黄色连衣裙的女士》《一个年轻的意大利女孩》,1870年
丢勒:《奥斯沃特·卡尔的肖像》,1499年,德国慕尼黑巴伐利亚州绘画陈列馆
可能比较搭的音乐
肖邦:《降E大调第二号夜曲》
肖邦:《第一号钢琴协奏曲》,A小调枯木练习曲
勃拉姆斯:《D小调第三小提琴奏鸣曲》
张新彬










 联系记者
联系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