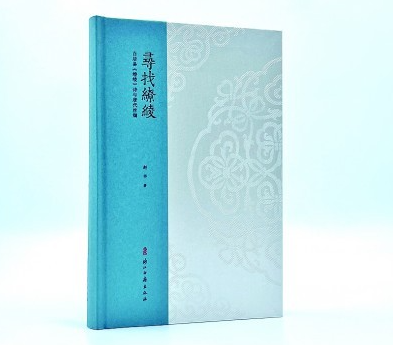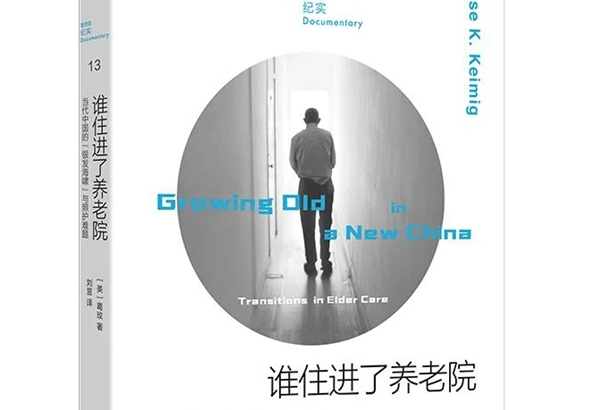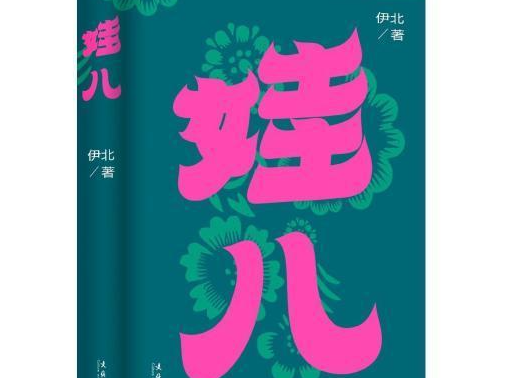郑州阅读人物志丨李伯谦:行走的阅读者

开栏的话:
在我们这个城市里,始终有许多人把读书和自己的生命融合在一起,把历史和当下的经纬编织在一起,用今天的光烛探幽过往的背影,又从以往的步履听到今天的足音,一直以这种样式构架城市的阅读姿态。
《郑州阅读》就是对这种姿态的一纸速写。

由作家齐岸青主编的《郑州阅读》一书,因人及物,由物至人,以随笔杂记的形式,记录与郑州这片土地有感情羁绊和生活经历的人物,形象描述郑州城市的前世今生和个体人生况味。书中记录了李伯谦、孙荪、张宇、马国强、李红岩、张广智、李佩甫、王澄、李韬等26位与郑州有过往、有故事的人。
即日起,正观新闻特开设“郑州阅读人物志”专栏,每天节选该书一篇文章,与读者一起品读品味那些“郑州岁月”。
今日编发第一篇:《李伯谦:行走的阅读者》。
引子
在我有限的人生经验和狭隘的认知里,总是很难以为郑州是个阅读的城市。郑州的街巷烟火给人印象显得散漫和疏躁,有时候甚至于透出些许粗粝。年少时每逢遇到下雨的日子,总会望着烟雨蒙蒙的窗外法桐树发呆,我小时候生活的街区是被它浓浓的绿荫遮蔽的,我知道一个女孩子把一棵树当成她的男朋友,她会时常走到那里跟它对话。那时候我总想象法桐树后,尤其是在黄昏雨后,街角或院落深处会有一盏始终为书亮着的窗灯,窗帘灯烛后面摇曳着掩卷的身影,这种旖旎的梦幻恰也碎在少年。我们这代人赶上了焚书禁书的荒唐年月,很长时间,阅读不仅是奢侈的而且还会是危险的。但我们这一代人又是
幸运的,青春时节又撞上色彩斑斓的20世纪80年代,书籍和思考是生活的荷尔蒙。
书是我们心中的树,尽管有时会有风雨,但它一直在那里。
个人的阅读与生活年代交指相扣,是我们读书岁月的特征。
郑州城市的阅读,永远不会像我期待的那样表现出细腻温润的情节,这是一个厚重博大的城市,喜欢在遥远的历史深处构架故事,“书生本色”在这个城市的日常话语体系里,谈不上会受到鄙薄,但也多少会有揶揄的味道。可是,你不能因此说郑州不是一个阅读的城市,读书的姿态在郑州,如同这方土地辽阔深厚的模样,要么是以风卷黄沙的气概飞扬,要么如同城市边际的大河用内敛含蓄的方式流淌。
2022年,疫情肆虐,中国一百个大中城市的阅读榜单数据排名里,郑州却悄悄把自己的位序从第二十三前移到十三。在我们这个城市里始终有许多人把读书和自己的生命融合在一起,把历史和当下的经纬编织在一起,用今天的光烛探幽过往的背影,又从以往的步履听到今天的足音,是这种样式一直在构架城市的阅读姿态。
《郑州阅读》就是对这种姿态的一纸速写。

郑州城市历史的零公里是从商汤王建立亳都开始的,三千六百多年来没有离开这个中心,阅读大概也是从那时候开始的。国人对汉字的认识多是来源于商晚期殷墟的甲骨文,甲骨文字闪亮登场时,已经是功能完备、成熟发达的文字符号体系了。常识告诉我们,任何成熟的东西都会经历幼稚的生长过程,何况文字的演变,更会有漫长岁月的镌刻,考古学指向,它的起源点应该在郑州。
1953年,在郑州商城二里岗曾发掘出土了两片疑似刻有文字的动物骨骼,是文字线索溯源的拷问。当年释读出其上的十一个字:“乙丑贞从受……七月又乇土羊”。但由于物证数量少,出土地层单位不清晰,骨辞的年代归属和是否属于文字的争议较大。孤例也难以为证,文字定性当时被搁置下来。
20世纪90年代,郑州市西北小双桥遗址,又发现早于殷墟甲骨文和青铜器铭文的朱书文字,使得我们重新去认识二里岗牛肋骨上“甲骨文”的价值。
小双桥目前发现的朱书陶文和刻画陶文,主要出土于宫殿建筑附近祭祀坑里的陶器上,表明文字与祭祀活动关系密切。朱书陶文书写上使用了朱砂并可能掺入了黏合剂,因此保存完好,字迹较清晰。文字类别丰富,包括数字、象形符文字、短语等。尤其是象形字特点突出,如帚、匕、旬、天、东等。小双桥遗址为郑州商汤立都历经十世之后,仲丁迁隞之都。王都兴衰更迭的路径即是文字演化过程,小双桥遗址的朱书陶文与郑州商城前后相袭,又和其后殷墟出土陶器上的刻画文字一致,为辨识史前文字提供了线索,也为后世文字话语体系成熟奠立基础,开始了中国文字的典册规范。
1991年,新密黄寨遗址又发现二里头文化的卜骨契刻符号,它和二里岗以及殷墟的牛骨刻辞,在卜骨材质、施灼、契刻象形文字特征上具有承继性,初步推测其中一字为会意,是表达设置机关捕兽。另一字,上部从目,下部从又(手),与相类构字要素的商代卜辞排列,似乎与凸显目、止的“夏”字形成联系。倘若如此,不仅将文字之源前推,也让我们苦苦寻找的中华之“夏”字更添实锤。

在郑州生活,你不去抖落这些历史的袋子还真的不可以,这么讲,郑州关于阅读的过往还真的是辽远。也许是因为早期文字的滋养,郑州除产生《诗经》《列子》这样瑰丽篇章和显赫的嵩阳书院之外,还有过伊尹、子产、潘安、杜甫、刘禹锡、司马光等等文人骚客,文化脉流如同大河之水滔滔不绝。直到大宋南迁,明清以降,文化的故事才渐以衰微。但郑州并未放弃自己的文化表达,明崇祯年间,知州鲁世任在郑州创立天中书院,算是低调为城市挽回一丝尊严。尔后,天中书院几经兴废,光绪年间,郑州知州王成德主持了已经更新为东里书院的复建工作,跟随他的一个书生徐世昌,从这里走出去,于光绪十二年(1886)中进士,后来入北洋,再后来当过民国的大总统。光绪末年,郑州北郊刘庄有个书生刘瑞璘,多年仕途后还乡。他于民国五年(1916)重修《郑州志》十八卷,并创办了郑州第一张报纸《郑州日报》。郑州这块土地上,就是这样始终有人走出去,又有人走回来,使得城市文脉未绝,始终坚韧地为这个城市文化血脉点燃、赓续香火。尽管书院旧址今天难寻,但“书院街”的地名还能讲述消逝的故事。

日子走到1956年,郑州市西北东赵村,一个叫作李伯谦的青年走出了村间的小路,行囊里北京大学历史系的通知书告诉他,此行甚远。可背负着母亲缝衲的布衣,又牵出昨夜“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的线绪,他又知道自己永远不会走远……

李伯谦 石战杰 摄影
六十多年后,李伯谦先生在给我讲述他去北京大学念书的故事时,曾给我勾勒过这样的场景:
当东赵村的灰瓦土屋、辘轳井、古槐树渐成远影,李伯谦第一次踏上绿皮火车时,眼前的一切都充满生动和新鲜。这个容貌有着羞涩感、内心却充盈着欢畅的年轻人捧书阅读,尽管狭促拥挤的车厢里,不停往来的旅客会打扰他的姿态,但窗外是辽远的田野和天空,风和日丽,自由飞翔的鸟儿牵出他的面容微笑和内心歌唱。
场景有些想象的成分,但至少我知道这是那年月通常的画风。
李伯谦的青春岁月恰逢共和国炽热梦幻的年代,他的少年之时未能跳出大多数青年的样式,做的是文学梦。读尽“红楼”,阅遍浪漫,上学时天天抱着小说,没事儿就写点煽情的小文字,人生目标就是成为一名作家。1956年从荥阳高中毕业高考,报的是北京大学中文系,却被历史系录取了。
走入北京大学的第一年,他拼命地阅读典籍文献、历史通论、考古常识,发现“历史和文学一样,都是迷人的”。尽管李伯谦说起他最终选择考古专业,只是受了老师说“学考古可以游历山水”的诱惑,在我看来,文学只是他的气质和姿态,他其实就是为考古而生的。李伯谦这一代考古人仿佛就是从泥土中长出来的,生活指定他们去把自己的命运无怨无悔地交付考古。
李伯谦是幸运的,他考古专业的老师可谓名师林立。教先秦史的老师是张政烺,早年因其在古籍文献的渊博学养,为胡适赏识,1936年北大毕业,便让他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思想史的一代宗师杨向奎说过:“在中国,听过张政烺的古文献课,别人的文献课就不用听了。”张政烺亦是藏书大家,晚年因医病筹措经费,此时已是北大考古系主任的李伯谦还争取补贴资金,购买他的部分藏书,这是师生多年后话。教历史的老师还有余逊,才华横溢,能将《汉书》全文熟背如流,是陈垣大师门下的“四翰林”之一,也曾为胡适的秘书。另有我国宋辽金史的一代宗师邓广铭,他也是胡适的秘书,追随过傅斯年、陈寅恪。考古方面的老师是吕遵谔,是红山文化、大窑文化的首倡者,也是遗址考古的主持者。吕遵谔的老师、旧石器考古开山大师裴文中先生也是讲座教授。教新石器考古的是在仰韶文化占据异常重要地位的大师安志敏教授。商周考古的开拓者邹衡先生教授夏商周课程。战国秦汉考古的先生是苏秉琦,是对中国文明起源最早提出系统学说的人,后来是李伯谦最为亲近的师长。创建水下考古的俞伟超先生讲授考古地层学和考古类型学。教佛教考古的开创者宿白先生,主要教授宋元考古等,他也是北大考古系第一任主任。
李伯谦的师长几乎都是中国考古学的开创者,排列展开就是中国百年考古学史的画卷。导师们给李伯谦的人生带来了巨大影响,他独立而求真的学术精神一生未改,渊源于此。
李伯谦就读北大的时间,也是政治风云变幻的岁月,他在不安静的日子里用读书给自己寻找了平静,其实李伯谦并不是刻意回避时代的风雨,考古是他的生命,他的坚守也是自我呵护。所以无论岁月如何纷乱,李伯谦始终给自己的内心摆放一张安静的书桌。
1961年毕业分配时,恰逢国民经济困难时期,安排工作非常困难,当时李伯谦没有幻想,他跑到昌平的考古工地实习,等待分配。后来,苏秉琦慧眼识人,他幸运地留校任教。留校后的李伯谦基本状态是从事田野考古,其间在1970年代帮助山东大学、南京大学成立考古专业。直到80年代,他才回到北大的课堂,主教商周考古。
回到讲台上的李先生,后来成为北大考古文博院的院长。北京大学的考古专业于1922年成立,最初叫考古研究室,马衡先生为主任,后来由胡适先生兼任。1952年北京大学历史系成立考古专业,苏秉琦先生出任考古教研室主任。1983年,北京大学正式成立考古系,宿白先生出任第一任系主任,以后严文明先生接任。1992年,李伯谦当了系主任。李先生到任的时候,北大的学科很多都改成了学院,考古系弱小一直,提不上议事日程。李伯谦先生另辟蹊径,他在1998年与国家文物签署合作办学协议,将北京大学考古学系扩办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又名“中国文物博物馆学院”,后来又颇费周折,才叫作考古文博学院,他在院长任上干到2000年。
还值得一提的是,在李伯谦任内,北京大学建立了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这座由美国友人捐赠的馆舍建筑在曾是圆明园附园鸣鹤园的旧址之上,鸣鹤园曾经的主人是徐世昌,历史让两个从郑州走出来的人有些恍惚的交映。
北大自1922年开设考古专业,对田野考古重视的传统便随之严格建立,在北大考古系学习,其他科目若不过,都能补考,唯独田野考古不过关不能补考,要留级。
不过踏足田野考古工地仿佛是李伯谦的天赋异禀,我多次领略到先生见到探方便精神抖擞、兴奋异常的状态。
1957年,入学不久,尚未有考古调查发掘经验的李伯谦,暑假期间回到东赵,在村子里转悠时,已经不再是儿时顽皮的嬉戏了,而拿出了未来考古学者的模样。他在村里村外一晃就是一整天,到处扒拉拣了几块陶片,并为此写过一篇小文,自认为这里可能是一座商代大遗址。
这应该算是李伯谦最早的自我考古实践和学术研究启蒙。可生活是一棵长满可能果实的树,青春的好奇、敏感和精力充沛让他充满想象,家乡的土地也给了李先生回报。2012年10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就在他当年捡拾陶片的地方,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发现了面积约一百万平方米的大、中、小三座城址,并确认了东赵遗址是夏商周完整连续的文化遗存。它和十多里之外的小双桥遗址构成了一个鲜活的夏商文明场景。2015年,东赵遗址入选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同时获得中国考古学会田野考古一等奖。家乡的土地和李伯谦先生整个考古生涯融合成为一个画面。
李伯谦第一次专业考古实习,是1958年参与了周口店遗址的发掘工作。从那之后,他从没有停下野外考古的脚步。从北边的黑龙江肇源,到南边的广东揭阳、汕头,西至青海西宁,东至山东泗水。特别是青铜时代的重要遗址如河南偃师二里头、安阳殷墟、北京昌平雪山、房山琉璃河、江西清江吴城、湖北黄陂盘龙城、荆州荆南寺、山西曲沃天马-曲村晋文化遗址,更是先生的考古重地。如今,他依旧记得在田野间跋涉、满身汗水尘土却乐在其中的日日夜夜。考古是他深入骨髓的热爱,每一趟出发,每一回紧握手铲、埋首探方,都会让他由衷欢乐。田野悄悄地磨蚀岁月,也铸就了考古学家李伯谦。
没有更多的时间在学校教书的李伯谦,尽管失去了许多著书立说的时间,可长期田野考古的实践却给了他学术思想的坚实基础,他的人生之锤总敲在学术思想的节点上。
1974年,他在江西省吴城遗址带队发掘时,形成他的《论文化因素分析方法》一说,文化因素分析方法是以类型学研究为前提,核心是比较研究,即在对于考古学文化遗存详细分解的基础上,同其他文化进行比较,以了解考古遗存的文化因素性质、演变、源流、交流、区系类型等情况构成。文化因素分析方法的产生可以追溯到1930年代,但最终成为考古学的一门方法论,应该是以俞伟超和李伯谦在1980年代对其进行总结而形成标志的,它和地层学、类型学一起构成中国考古学实践应用的三大方法。
中国以往有文献记载的“信史”仅于西周共和元年(前841)始,此前的历史年代没有一个公认的年表。1996年5月16日,旨在研究和排定中国夏商周时期的确切年代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来自历史学、考古学、文献学、古文字学、历史地理学、天文学和测年技术学等领域的一百七十名科学家进行联合攻关,李伯谦任专家组副组长、首席科学家。2000年11月9日《夏商周年表》正式发布,断定夏代始年为公元前2070年,商代始年为公元前1600年,盘庚迁殷为公元前1300年,周代始年为公元前1046年。夏商文化从此由虚无缥缈的传说逐渐变成了清晰可见的历史真实。
“夏商周断代工程”结束之后,李伯谦先生又主持了为期三年的文明探源预研究,他将自己的研究视野投向了“原初的中国”,直抵文明源头去叩问。
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始于我们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它和史学中的五帝时代、考古学中的仰韶文化时期对应。黄帝究竟是信史还是传说?这是古代文献研究和现代考古实证的待解之谜。文字出现之前,世界区域的文明史几乎都是口碑神话传续,也许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令人疑信参半的神奇传说,才使人类文化记忆瑰丽而神奇、丰富而精彩,李伯谦相信,它也是我们历史的真实存在。
两千多年前,司马迁撰写被后世尊为中国第一部信史的《太史公书》时,世间关于黄帝的事迹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司马迁曾亲游各地,考察古迹,披阅文献,删减各种矛盾离奇的传闻,采用最可信的内容,给我们留下一个具有史实意义的人——黄帝。
在文明探源预研究中,李先生和他的朋友如同持灯者,穿越夏商王朝的历史隧道,探索中国文明的起源,努力给五千年的文明历史勾画图谱。这以后由王巍先生和赵辉先生领衔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历经十几年艰辛探索,终成正果,揭示五千年文明史起承转合的清晰脉络。
尽管黄帝时代如椽之笔的宏大叙事,至今依旧给我们留下无数的谜团有待考证,但今天人们在疑惑、欣喜的交替往复中,依然能触碰到那些曾经真实的片段和体温。中国土地上关于黄帝的遗迹和传说已成为我们文化最为丰富的宝藏。黄帝时代开始了堪称“国家”的雏形岁月,承负了文明缔造者的责任,中华文明几乎都是循着黄帝的脚步前行,无论怎样解答这段历史,黄帝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象征和符号,他的故事和形象是闪烁在中华大地上那段文明初创时期里最温暖的光泽。
如果缺失了这段令人充满想象的历史阶段,中华文明便不可能在短短的一千多年后,经尧舜禹、夏商周迅速走向成熟。更不可能在春秋战国时期,一个个脱胎于黄帝时代智慧核心的伟大思想横空出世、泽被千秋。以黄帝为代表的那个时代,是中华文明的源起,更是一段真实历史上演的传奇。
在对文明进程的阶段探考中,李先生和中国大多数考古学家基于对中国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乃至早期铁器时代的研究,基本认同中国文明和国家的起源、形成和发展的阶段,是苏秉琦提出的“古国—方国(王国)—帝国”三大阶段。
在研究中国文明演进过程时,李伯谦逐渐把他的重点放在研究文明演进的模式和路径上,李先生在他的《文明探源与三代考古论集》一书中,提出了中国古代文明演进的“两种模式”,文明形成的“十项判断标准”,文明进程的“三个阶段”等重要学术观点。
考古学上如何判断文明标准?李伯谦从大型聚落出现及分化,围沟和城墙等防御性设施,大型宗教礼仪活动中心和建筑,墓葬分化和特设,专业手工业作坊和仓储设施,武器和象征最高权力的权杖、仪仗等器物,文字及使用,异部族文化遗留,聚落统辖关系,聚落文化辐射等十个方面,提出自己的文明判断观点。
他更富有创见地提出了中国古代文明演进的“两种模式”,即“神权与王权”。李伯谦着重指出,距今五千三百年前后,仰韶文化、红山文化及良渚文化先后进入了高于部落之上的、稳定的、独立的“古国”时代。各地“古国”选择了不同的发展道路或演进模式。中原地区“仰韶古国”表现的是以军权和王权为基础的王权道路,“红山古国”则选择了神权道路,“良渚古国”选择的是由军权、王权和神权相结合并突出神权的道路。以神权为核心的演进模式是崇尚祭祀奢华、耗费社会财力“竭泽而渔”式的发展,后续发展动力显然不足;以世俗化的王权为核心的演进模式却是更务实、更加稳健,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具有较强且持久的发展动力。因此,原来繁荣的中心聚落萎缩下去,而相对落后的中原地区却慢慢发展起来,最终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形成华夏文明的根脉和主干。
关于夏商周断代、文明起源、仰韶文化分期和发展模式,是先生毕生的智慧和心血,他也因此在考古学史上写下自己的名字。
日月如梭,当年英气勃发的少年如今已是著作等身、桃李满天下的学者。几十年后,白发霜染的李伯谦先生又沿着当年走出去的路,回到他的故乡城市,无论说是叶落归根的情怀,还是人生归属宿命,他从这儿走出去,最后又回到这儿来。河洛的水流始终在这块土地上书写这样一个的人生轨迹。
回到家乡之前,李伯谦把他大部分的藏书做了整理,捐给了郑州文物考古研究院。心无物役,他把相伴几十年的书安顿了一个居所,也给自己寻到一个心灵回归之处。缘此,与他相濡以沫的夫人张玉范教授和宝贝女儿也把大部分生活时间赠予他。一生行走田野的李伯谦,及至晚年才和家人构筑了一个朝夕和煦相伴的空间。
先生对我说,我这以后啊,就只做两件事了,一个是河洛古国,一个是天中书院。
我清楚地知道,考古是他的执念,一种亲近的欢喜。这种欢喜,让他心无旁骛,思考也就如同恣肆汪洋的黄河,奔腾不羁。先生永远充满生命力。
双槐树遗址是河南也是黄河流域仰韶中晚期规模最大的中心聚落,其三重环壕布局,具有中轴线意义的大型宫殿式建筑、池苑、广场、瓮城和等级分明的墓葬都十分罕见。聚落具备了早期文明都邑的性质,它和郑州周边的汪沟、青台、西山、大河村等仰韶文化遗址构成了一个体系完整的古国形态。李先生反复征求考古学家意见,久经思索,打破考古学界用最小地所命名的常规,用“河洛古国”命名了这个仰韶文化的核心地域。我个人总以为这是神来之语,它让历史的时间和空间在这一刻交融定格,使得我们考古探寻变得和煦明朗,意味深长。
天中书院是城市历史深处的文化内蕴,先生倾注心血,希望它的重建给予古都更多斑斓的色彩。
先生的话语如丝,绵似细雨。这种岁月沉淀下来的安然与温和,是建立在他的精神富有和充实的位置之上的,你如果乐于享受,也就在他的场景之中了。
在编辑先生的文集时,我翻看了不少他的日记、书信、照片,他的这些日常生活中的文字、图片,让我更能直接触碰到先生的睿智、慈悲、温暖、情趣和率真,很多时候它比先生的学术文论更能打动我。
先生望着他这些刻画着岁月印记的版本,总是略显严肃地说,你要写我,不要只是赞扬,那些幼稚、谬误的事情都要如实去写!
一个人抵达崇高,是这岁月叠压之后的自省救赎,它能让人具有从容的纯粹真实。
不过回忆往事时,看见更多的总是先生的笑容。他总是含着微笑,自然亲切,这种善意是尘封的记忆之页,偶尔被翻动一下,也只是为了抹去灰尘。李先生开怀大笑时,又会让人动容,看似孩子般的天籁,这样的场景,你会有难以抑制的暖流在心中涌动,滚烫而熨帖。
李伯谦先生是一位走近便可以感受的人,他的微笑就是世间的箴言。
李伯谦是一位行走着的阅读者,你去认识他,也是阅读一本厚厚的书。
李伯谦
1937年生于河南郑州。考古学家。历任北京大学考古系主任、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兼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馆长等。参加和主持了河南偃师二里头、安阳小屯殷墟、山西曲沃晋侯墓地等多处遗址的发掘,为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项目首席科学家、专家组副组长,主持国家“十五”科技攻关重大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课题。出版专著《中国青铜文化结构体系研究》《商文化论集》《从古国到王国——中国早期文明历程散论》《感悟考古》等多部,主编《中国出土青铜器全集》(二十卷)。
(《郑州阅读》由河南文艺出版社2023年9月出版)
郑州海昌海洋旅游度假区将9月28日盛大启幕,“”鲸“”奇世界 闪耀中原!
让青春在志愿服务中发光发热——团郑州市委组织青年志愿者服务2023中国(郑州)国际旅游城市市长论坛
金水区凤凰台街道召开2023年“99公益日”暨“慈善日”活动动员会





 联系记者
联系记者